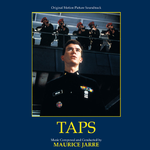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这个还用得着学吗
老娘儿们不是天生就会煮饭烧菜吗
啊
我说库兹满
你这一辈子见识真不少呀
可是既然这儿没有鱼
你当渔夫干什么呢
老爷
我没什么可怨的
干这个这真是要感谢上帝
这里还有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家伙
叫安德烈
普贝尔
女主人说他白吃饭是罪过
硬派他到造纸厂的积水房干活
普贝尔还盼着他有一天会发善心呢
他有个表侄在女主人的办事处当办事员
答应为他向女主人求个情
说什么情呀
我亲眼看到普贝尔给他的表侄下跪磕头呢
你有家眷吗
成过家吗
没有
姥爷已去世的达己亚
纳瓦西里耶芙娜祝他进天堂
绝对不许任何下人结婚
他总说
我单身过不也很好吗
干嘛结婚
瞎胡闹
那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有工钱吗
有什么工钱呀
饿不死就很知足
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女主人长命百岁
涅尔莫莱把船修好回来了
他让苏奇卡赶紧跑去拿膏子
在我跟这可怜的老头聊天时
弗拉季米尔不时的带着鄙夷的神情望着他
这人有点傻
苏奇卡走开后
他说是一个没半点教养的人
一个乡巴佬
他连家谱也够不上
尽是瞎话
他怎么能当得了戏子
你想想看
跟他聊天真是白劳神
大约过了一刻钟
我们已经坐在苏奇卡的平底船上了
我们觉得不太对
没劲
但是猎人向来都不讲究
苏奇卡站在船尾
用高撑船
我和弗拉季米尔坐在横搭着的一块船板上
涅尔莫莱坐在船头
虽然船缝用麻屑堵上了
但我们脚下很快就渗上水来
幸好没有一丝风吃
池塘仿佛睡着一般
我们的船像爬行一样
老头子苏吉卡从烂泥中费了好大劲儿拔出膏来
上面还缠满了一条条的水草
睡莲那繁密的圆叶子也阻碍着船的前进
当终于到达了芦苇丛后
这里一下热闹起来
野鸭由于我们突然侵入他们的领地而大为惊慌
鸣叫着腾空而起
枪声立刻砰砰的响起
眼看着这些短尾巴的飞禽在空中翻着跟斗
扑通扑通的重重到栽进水中
那种情形真叫人快活
当然
我们无法把剩下的野鸭全都弄到手
一是伤青的一下子钻到水里去了
二是有些被打死了的
都掉到茂密的芦苇荡里
即使涅尔莫莱那尖利的眼睛也找找不到他们
尽管如此
快到中午时
我们的小船上已经装满了野鸭子
令涅尔莫莱大为开心的是
弗拉基米尔的枪法极不高明
他每次打控之后
他就装出惊讶的样子把枪检查一下
显示他的枪不好使
最后再找出许多没有打中的理由
聂尔莫来照例谈武虚发
我照例打的不准
苏奇卡则照例用替主人效劳的那种眼神看着我
不时大喊
看那边
那边还有一只
他还不时在背上搔痒
不是用手来
而是靠牛抖动肩胛骨来止痒
天气特棒
在湛蓝的天空中
一团团白云缓缓的飘动
清晰的倒映在水中
四周的芦苇随着清风沙沙作响
水面在艳丽的阳光下像钢铁般闪亮
就在我们准备返回村子的时候
突然乐极生悲
其实我们早就发现
河水一直慢慢的渗进我们的小船
越积越多
我们让弗拉季米尔用瓢往外舀水
那水瓢还是我的猎尸有先见之明
从一个在打瞌睡的农妇那里偷来
以备不时之需的
在弗拉季米而一直履行自己舀水的职责时
情况还好
可是到了打猎快结束时
那些野鸭子好像有意要向我们道别
一群群的飞了起来
又使我们忙着射击
却忘了小船渗水
突然
聂耳莫来猛的一突
竭力向想抓住一只被打死的鸭子
全身压向船的一侧
这只小破船便随之倾斜
灌进很多的水
迅速沉向塘底
幸亏是在水不深的地方
我们惊呼起来
但是无济于事
我们都站在没到脖子的水里
满团的死鸭子漂浮在我们的四周
就是现在
想起当时我的同伴们一个个都吓得脸色煞白
就感到有些好笑
不过说实话
在当时我是没有心情笑的
我们每个人都把枪举在头上
苏奇卡大概是模仿主人成了习惯
也把长篙高高举起
这是不是真正好笑的
涅尔莫莱第一个打破这沉默而惊恐的局面
他开始说话了
呸 糟透了
他往水里唾了一口
把火都发到苏七卡身上
都怪你
你这叫什么喘哪
苏奇卡老头只剩下连声道歉
你也够行的
涅尔莫莱转过身来
责备弗拉季米尔道
你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不咬水
你 你
这个时候弗拉季米尔也顾不上反驳了
他冷得像筛糠一样
全身颤抖
上下牙齿打架
无奈的苦笑着
他的伶牙俐齿
高雅子尊全没有踪影了
那该死的小船在我们脚下微微晃动着
刚掉到水中时
我们觉得水很凉
但很快就习惯了
最初的那种恐惧过去之后
我便环顾四周
发现我们十几步之外全是芦苇荡
芦苇的远方是谈案
我们怎么办呢
我问涅尔莫来
总不能在这儿过夜
他回答说
他让弗拉季米尔拿着他的枪
弗拉季米尔乖乖的接过了去
我去探探浅的地方
涅尔莫莱很有信心的说
好像每个池塘都必有浅滩
他拿过苏奇卡的膏子
小心的探着水
朝岸边射去
你会游泳吗
我想他
不 不会
他的声音从芦苇荡中传来
呀
这会淹死的
松奇卡淡然的说
他其实不怕危险
而是怕我斥责他
这会儿他不再担心了
只是偶尔喘两口大气
表现出没有必要去摆脱当时的困境
过了一个多小时了
涅耳莫菜还没踪影
这一个小时我们觉得特别漫长
开始我们还和他频频的相互呼应
后来他对我们的回应逐渐少了
最后竟然声息全无了
村子里想起连绵的晚岛的钟声
更加重了我们的愁绪
我们彼此无话可说
也不想对视
我们的身体逐渐发僵
饥寒与疲累交迫
苏奇卡眨巴着眼睛
随时都要睡着了
在漫长的等待中
涅尔莫莱终于回来了
我们三个高兴的无法形容
抢着探问情况
涅尔莫来带来了好消息
我到岸边了
鹿看到了
快走吧
我们真想立即就动身
但涅尔莫菜却从没在水中的口袋里掏出绳子来
把一些水鸭子的腿逐个系上
用牙齿咬住绳子的两端
然后才徐徐前行
弗拉季米尔
我 我 苏奇卡
老头跟在他后面
依此鱼贯而行
离岸边约两百来步了
涅尔莫来便一步不停
放心大胆的走了起来
只是不时的高声提醒我们注意右边的大坑或左边的陷泥
有的地方水没过了我的脖子
可怜的苏齐卡个子小
有两次呛了水直吐白沫
涅尔莫来凶恶的对他吼
苏奇卡听了竭力往上窜
终于踩到水浅的地方
即使在危急的关头
他也没敢抓我大衣的衣襟
我们四个人终于筋疲力尽的到了岸边
一身污泥
成了名副其实的落汤鸡
大约过了两小时
我们已经想方设法把衣服弄干了
正坐在一间宽敞的干草棚里准备用晚餐了
马车夫夜鼓继耳
站在大门口诚心诚意的请苏奇卡吸烟
苏奇卡猛吸起来
看样子吸的很过瘾
弗拉季尼尔已经很疲乏
歪着小脑袋很少说话
涅尔莫莱在专心的擦拭我们的枪
几只狗在四周将尾巴摇得更欢了
焦急的等着喝燕麦粥
马在屋檐下跺蹄嘶鸣
太阳就要下山了
余晖染红天空
金黄色的云朵散布在天空
越飘越细
如丝如缕
宛如梳洗过的金色羊毛
这时
村子里响起了阵阵悦耳的歌声